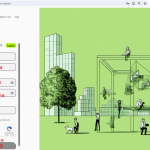從《英雄》到《影》:張藝謀的權欲與抗爭 轉自:多維網
跟《英雄》比,《影》走的是截然不同的方向
《影》不可避免要被拿來和《英雄》比較,它們雖然在價值取向上截然不同,卻都具有獨特的美學風格。張藝謀自己對《影》和《英雄》的衝突也心知肚明,在接受採訪時他說:“在創作《英雄》的時候,那個故事更追求的是金庸所謂的‘俠之大者,為國為民’,江山社稷比草民的生命重要得多。而這次《影》則完全是一個個人化的故事,我把‘人’,放到了歷史的底色之上。” 告別宏大敘事的張藝謀變得更加從容,也更加可愛,這和他拍攝《長城》時的束手束腳、籌備奧運會開幕式時的愁眉緊鎖截然不同。張藝謀這一次松下了鐐銬,達到了本世紀以來他最自如的創作狀態。 對老謀子的影迷來說,《影》是一次熟悉的回歸,它不只致敬了黑澤明和《影子武士》,還是張藝謀過去電影中的經典元素的延續。從刺殺與境州蓬勃的生命力,我們看到《紅高粱》裏餘占鼇刺殺李大頭的影子;從電影裏化不開的濃稠血色和綿綿細雨,我們看到《活著》裏小人物的悲劇;從靜謐灰暗的密林,則分明可見《十面埋伏》裏的竹林情懷。還有經典的囚禁空間、三角權力關係和“噬父”主題,張藝謀用《影》告訴世人,那個熟悉的自己又回來了。而且這一次,他變得更加決絕。 要談論《影》在張藝謀電影世界中的地位,就需要回顧他過去二十年的創作。縱觀張藝謀過去二十年的創作,其關鍵字是“宏大”。從2002年的《英雄》開始,張藝謀走上了追求宏大之路,到《長城》達到高潮。當中儘管還有純情的《山楂樹之戀》和《歸來》這樣的傷痕題材,但更被人熱議的終究是《英雄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、《長城》等。 從山雨欲來風滿樓式的千軍圍城,到極盡豔麗之能事的帝國景象,張藝謀迷戀起一種“東方紅”式的美學,具體的個人表達反而被淡忘。這條路的極致就是中美合拍片《長城》,個人乾脆成為報表數字一樣的雞肋,人海戰術在轟鳴的音樂中屢屢上演。造作的臺詞,仿漫威英雄的配置,好萊塢的商業模式和張藝謀的組合被證明是一場浮誇的宴席。《英雄》:犧牲個體成就集體
《長城》遭遇差評,但它還不是張藝謀最富爭議的電影,張藝謀最有爭議的電影是《英雄》,就連他的老同學陳凱歌也不買賬。陳凱歌說:“說實在的,我不喜歡《英雄》這部片子。我看這個電影很有問題。這部片子是空的,我不喜歡它的主題。我自己也拍過‘刺秦王’這個題材,可是我們(拍攝)的結局截然相反。我不認為犧牲個體生命成就集體是對的。” 《英雄》講的是一個劍客放棄刺秦的故事。劍客無名計畫刺殺秦王,卻最終放棄。秦王為何不可殺?電影給的答案是“天下“——“七國連年混戰,百姓受苦,唯有秦王才能停止戰亂,一統天下”。這種“天下”觀統合了《英雄》的敘事,在無名放棄刺殺秦王那刻達到高潮。 《英雄》上映時非常招人恨,很多觀眾覺得張藝謀在給暴君唱頌歌,違背藝術創作者的良心。張藝謀很委屈,到2007年他還惦記著這事,在一篇叫《士為知己者死的過程最動人》的文章裏,他強調自己很欣賞俠文化,不是要歌頌暴君。 他還透露《英雄》最初有另一個結局:劍客無名放棄刺殺秦王,離開時卻被射殺,群臣俯首高呼:“恭喜大王又躲過一劫!”秦王嬴政流下眼淚。張藝謀後來刪掉了這個結局,他說:“如果做了這樣的顛覆,秦始皇一代梟雄的形象是得到了鞏固,也使得他非常有智謀,一切都在帝王的掌握之中。但是這麼做的話,和我原本的意圖就相悖了,梁朝偉他們的犧牲會變得非常可笑。” 然而,很多人依然對《英雄》不買賬,因為這部片子有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,張藝謀將“一統”作為俠的最高價值取向,他卻忽略了俠文化和專制皇權的根本矛盾。秦是中國皇權文化的開端,秦始皇要在經濟、政治、思想、文化上“大一統”,但俠以武犯禁,挑戰國家機器,這種江湖異端必然是中央政權的“眼中釘,肉中刺”。 武俠本身就有別於大一統的價值取向,文人墨客們歌頌武俠的仗義相助、鋤強扶弱,是因為大一統的專制政權並不能從根本上保證百姓的權益,這時候,百姓就會盼望一個第三方的正義力量,能夠踐行他們心中的善來懲治惡,這個踐行者正是武俠。可在《英雄》裏,無名卻假“天下”之名,認可了秦王的大一統觀,而秦王雖然尊敬他、欣賞他,卻依然默許秦兵射殺無名,這個結局就彰顯了俠文化與大一統敘事間的衝突。《影》:虛擬世界中的權與欲
《長城》讓張藝謀跌了一跤,也讓他暫時告別了宏大敘事,於是有了這一部《影》。在這部電影中,主人公子虞為了篡權奪位,圖謀境州,並暗中培植替身;另一邊,鄭凱飾演的沛王表面暗弱,實則權欲極強,一直想剷除子虞,鞏固皇位;而另一位主角,也就是子虞的替身“境州”,則完成了一次影子到真身的蛻變。他們都被權力一邊誘惑,一邊煎熬著。 延續著過去的主題,《影》裏面人物的欲望無所遁形。陰雨、深宮、暗河、奴役,環境有多壓抑,欲望爆發得就有多強烈,這不單能從境州與子虞的博弈中看出,小艾的性本能和長公主反抗命運的嘗試也彰顯了這一點。張藝謀不再用“天下太平”等大詞粉飾人物的欲望,他要暴露的就是赤裸裸的人本身,一個拒絕“雞湯”的殘酷世界。 《影》撲面而來的是權力狡詐,以至於有人認為這是一部純粹的權謀片,然而,《影》實質是一部具有多重意味的電影,權謀只是浮在最上面的一層油。《影》有趣的是它的“不響”。比起劍拔弩張的大段對白,“不響”之處才是《影》更有餘韻的地方。 張藝謀利用大量的道具代替了人物的對白,太極、琴瑟、山水、陰陽、雨水、竹傘、面具乃至箱子,從電影的第一幕開始,道具就代替人物在發聲。琴瑟和鳴中的矛盾與心亂如麻,代表了小艾與境州曖昧的關係。簾外一刻不停地下雨,將氛圍推到一個潮濕、壓抑又暗流湧動的極點。電影在給人物特寫時,時時傳出琴弦之音,不同的旋律傳遞出不同的心境,《影》處處“不響”,又處處在“響”。 如學者李強所說,張藝謀擅於把握封閉空間裏的權力關係。“《紅高粱》裏的酒莊、《菊豆》裏的染坊、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裏的大院、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裏的王宮、《金陵十三釵》裏的教堂”,以及《影》的密室,張藝謀虛擬的空間壓迫、逼仄、光線極不平衡,充滿了對人肉身的限制與壓抑。 空間的壓抑讓欲望的迸發成為可能,也塑造出極致而變態的權力關係,《影》裏面的境州正是這樣一個異化的典型。他原本的訴求很簡單,只是想和母親重聚,通過完成任務換取自由,但在密閉空間生存過久,經歷過一次次爾虞我詐和真身的欺辱後,他開始了自己的轉變。 與小艾的肌膚之親代表著欲望的覺醒,母親之死則象徵著一個靈魂的失去和再造。自那夜之後,一個更冷酷更殘忍的境州出現,他學會了權變詭詐,學會了爭奪自己想要的東西,卻發覺欲望是一條填不滿的深溝。 到結尾時,境州已不是從前的境州,而是又一個“子虞”。諷刺的是,這些囚於鐵屋子裏的個人沒有徹底的反抗,只有對主人地位的爭奪,他們的行為反而強化了鐵屋子裏的秩序。城頭大旗易,壓迫與被壓迫的格局猶在,反反復複下來,不過是誰當主子誰做奴才的區別。今天境州取代了子虞,成為新的真身,明天又是否會有新的影子,來重複昨日的命運呢? “人心似影。”記得有人採訪張藝謀時,他用這一句話來概括全片。影子是灰色的,就像電影介於黑白之間層層疊疊的灰一樣,張藝謀探討了人的複雜性。真身和影子之間,真的那麼黑白分明嗎?或者說,我們想要呈現給別人的樣子,和我們自己,具有怎樣的關係?電影中,張藝謀借人物之口說:“真身沒有了,影子就無法存在。”而影子若消失,真身也將赤條條地顯現出突兀。 如果說在宏大路線上,張藝謀因為無法處理好廟堂與民間、集體和個人的分寸而進退失據,那麼在水墨丹青的《影》裏,張藝謀反而重拾了他的自恰。也許,當夜深人靜時,張藝謀回首自己這些年的創作也會百感交集。把他折磨得翻來覆去的《長城》票房口碑都不行,倒是《影》成了自己近十年最拿得出手的作品。]]]]> ]]>(Visited 63 times, 1 visits today)